拈花微笑,从释永信事件说起
这几天河南天气很热,燥得人心不安,比气温还热的是嵩山少林寺的林林总总。
一、修行与功德
短短一周,少林寺变了天了,先是这大和尚被公安带走,后续戒牒被佛教协会取消,然后新方丈入主少室山。从正式通报来看,经济问题为主,还有违反戒律的情形。
眼见得金钟罩铁布衫好似破了功,仿佛庙堂之上的金贵物件碎成了片片渣渣,乌泱泱、轰隆隆,一时间舆论哗然,全球瞩目。恍惚间,小说里的恶言竟也成了谶语。这一次蒙羞的何止古刹少林,仿佛对汉传佛教的信任危机也像塔林砖缝里,那些经过风吹雨淋之后,默默发了芽的无名枝叶。
好多信徒一时间更是不可接受,心中憋闷,好像拜来拜去那金光护体的,一下子光环褪去成了草胎泥塑,这让一颗心如何着落?!还有那曾经不分昼夜手抄经文的,好容易得到了收录,一时间签字背书的人除了问题,仿佛自己积累的善缘荡然无存,更有一种受了诈骗的感觉翻涌而出。
大可不必,大可不必。功德也好,业障也罢,都是自己的因缘,在佛陀看来,世人本俱佛性,只要破除无明(阻碍认识世界与反照自我的不良信源或不好的思维方式),就能觉悟。将自己的修行全赖于他人的认同,本身也是一种“无明”啊!
虽不可否认,原来的那大和尚确实违背了“三皈五戒”,其袈裟在身却凡心未了,免不得落个千夫所指。但是,一人的迷惘所致失其本心,也只是种因得果,他影响不了汉传佛教对世界的理论贡献,也不会影响中原禅宗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历史地位。

表面看来,释永信对于嵩山少林寺是个光复者,从门可罗雀到香火繁盛,他刘某人作为火车头不是一无是处。可别忘了,唐三藏不是因为穿了锦斓袈裟成了唐三藏,就像大学是大师之谓而非大楼。对于大众来说,被过度商业化的不讲因缘讲银元寒了心,没有慈悲哪有清净;对于佛法来说,释永信更是堕入了颠倒梦想,从破戒到积重难返,以至注销戒牒,都是他一念之间入了邪道的结果。
有人说,他让少林成了中国功夫标签而蜚声国际,他扩建少林寺,盖庙宇、立碑修塔,让僧众人数涨了好多倍。难道这不是大功德?且不论,这是否对千年少林文化IP进行了透支提现,他是否有功德呢?并无功德。非是妄论,这个问题一千多年以前有人问过,就是梁武帝。公元527年,达摩从广州上岸来到中土,受梁武帝邀请来到建康(南京),梁武帝一脸虔诚,说我举国之力大建寺庙,供养僧人,家家户户我都让他抄颂佛经,这算不算大功德?达摩说,毫无功德。
乍听起来达摩有些不近人情,但是达摩作为禅宗二十八祖来到中国,他清楚地知道,自己不是验收土木工程或者看书法来了,而是点一盏心灯,以心传心。
为何毫无功德?因为路线方向错误,离经叛道了。歌里都唱过,观念不合格,其他不及格。就达摩看来,梁武帝修庙兴佛是他自己的业力所致,而非发愿觉悟,更没有让民众觉悟得解脱得快乐,反而大兴土木、大肆供养,让大众深陷苦海。这种令众生迷惘的苦难,正是佛陀之所以放弃王子身份去寻找解脱之法的直接诱因,梁武帝所为与佛心佛性相悖、与大乘观念相左,必定无所收获。从禅宗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理念来看,那释永信也是背弃了佛门教义,如此便是做得多,错得多。
二、小乘与大乘
我们从头理一理。首先明确几个基本概念,什么是佛法,什么是佛教,什么是禅宗,什么是禅学。佛法是佛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理念构架,佛教是基于佛法的社会化组织和管理体系,禅宗是佛教的一支宗派,禅学是禅宗修行的理论果实。打个比方,佛学是种子,佛法是根系,佛教是具象了的树干,禅宗是树上支干之一,禅学是这一支上开出的花朵。

那什么是小乘佛法、什么是大乘佛法呢?小乘是度自己,大乘是把度自己的事情放到度世人的普度众生大事业之中去,你度了众生之时,也早就度了自己。这是一种“她在丛中笑”的境界,当全人类获得解放,你挥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小乘之于大乘,是小康和大同,是独乐乐和众乐乐,是有我和无我的境界。大乘佛法的心境,用一些实业家的话来讲,做好事业服务社会,成功只是这个过程中的附属品。当然,佛教没有因为大乘而否定小乘,反而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,所谓大行不顾细谨,比如在佛陀开悟前,他们一行几人来到了位于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处苦行林,就是修炼场所。当时,佛陀奉行的修行方法便是苦修,他那时认为身体的舒适性和灵魂的自由度成反比,所以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,以求得灵魂的大彻大悟。在林子里打坐七天,就吃了一点米,弄得“身形消瘦,有若枯木”,还是没有证悟。
这里解释一下“证悟”,证悟是对理论的“实修亲证”。悟是大觉悟,你想通了破除无明的办法,证是对这个思维体系的论述和验算的过程,而且要有普适性。比如,佛陀本是王子,如何脱离现实痛苦,他说他回家就有钱花,这不叫“证悟”。因为和他一起修行的可能是一个穷苦人家孩子,他回家等待他的依然是饥饿和毒打,这个“悟”就没有一般解,就无法得“证”。所以,佛教说人人皆有佛性,就是承认人与人、人与万有之间的“同一真性”,这是证悟的内在要求。
好,回到佛陀的苦行林里,这天不知不觉到了腊月初一,释迦牟尼实在顶不住了,又饥又渴又困,抬眼皮都费劲。这时,佛陀心中憋闷,就跟自习室里坐了一天,就这一道大题没想明白一样。他于是走出了苦行林,跳进旁边小河给自己洗了个澡,想换换脑子。恰巧,河边一个附近村的放羊妇女,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修行者,又一瞧这人走路直打晃,就端来一碗乳糜,乳糜就是牛奶里面掺了点碎肉,王子一想,人是铁这饭是钢啊,喝吧,再不吃点撑不过明天。于是端起碗一仰脖喝了个精光。和释迦牟尼一道来的五个苦行僧,一看他喝了这碗供养,齐声说,乔达摩悉达多,你这道心崩坏啊,于是扭头离开了他。佛陀没放在心上,继续回到苦行林,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入了禅定,七天七夜之后成道了,这一天是腊月初八。嗯,腊八节吃腊八粥就是为了纪念那改变世界的一碗牛奶。

这里还得说一句,佛陀没有因为自己要行大道而否定了离他而去的五个僧侣,如果因为要弘扬大乘去规定了、否定了小乘的修行法门,那也是一种我执。
三、拈花微笑
好,话说回来,如果不是在禅宗祖庭的少林,如果释永信不是少林方丈,这件事不会如此备受瞩目。那我们还得理一理,禅宗是怎么个事儿?
达摩是中国禅宗的一祖,却是古印度禅宗第二十八祖,也叫西天二十八祖。那禅宗初祖是谁?有人说了,那还用问么,肯定是释迦牟尼啊。可不是,禅宗初祖是摩柯迦叶(“叶”音“射”),也就是佛陀大弟子,迦叶尊者。
这里不得不说起一桩禅宗公案,也是禅宗的开端,叫“拈花微笑”,就是“拈花指”那个拈花。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记载,“世尊拈金婆罗花示众,八万四千人天悉皆惘措,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云:我有正法眼藏,涅槃妙心,实相无相,微妙法门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付嘱摩诃迦叶”。说的是,在佛陀晚年一次灵山法会上,释迦牟尼一语不发,只自己轻轻地拈着一枝赤色树花,向在场听众环视一转;当时,大家都不明白佛陀用意,面面相觑、不知所措,唯有摩诃迦叶尊者会心地展颜一笑。于是,佛祖就当众说道:“吾有正法眼藏,……,付嘱摩诃迦叶。”

佛陀说的话什么意思,我有一套正藏佛法,正藏就是核心课程,而且是有独立的、完整的理论体系,不是辅修课。法眼是什么,法眼不是肉眼,是一种“本质直观”的本领,还记得《心经》开头么?“照见五蕴皆空”,这就是法眼的本领,它不是先验的,也不需要论证,它是超验的直觉。通过法眼就能进般若境界,所以叫涅槃妙心,这是说禅的妙用,禅是入般若得涅槃的灵巧法门;同样因为法眼就能不住相。微妙是说它精深奥妙,所以不立文字。因为这种哲学的境界不能通过语言或者文字来承载,于是“教外别传”,这里的“教”不是说佛教,而是指传统的“经律论”的讲授形式,要区别于这些言传身教,而是机缘之下以心传心。
所以,佛陀拈花之时没有语言,但是摩柯迦叶明白了佛陀的心,一花一世界,花不是花,只是人们愿意管它叫花,它现在是一朵花,只是因缘使然。它的内核与芸芸众生一般无二,它是上一个时空的我,或许是下一个时空的你。它是极小,它是无穷,它的灿烂是因为你的心感应到了它的存在,它成了一朵花,就包含了所有的道理,那你们还在等我说出什么呢?语言描述不了它的精妙,文字概括不完它的内涵,用语言来说一件事物,用文字来框定一个状态,这时的文字和语言就成了无明,用文字和语言的人便有了分别心,就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。
四、百姓的佛法
说回少林。达摩在嵩山石洞之中,播撒下了禅的种子,但二祖慧可并非少林寺僧人,得法后便离开嵩山。实际上,直至元代雪庭福裕法师将禅宗曹洞宗定为少林正宗,少林寺才真正的由律转禅,由此才有少林寺的“禅武不二”。
相传二祖慧可在其晚年于安徽潜山一带传衣钵于三祖僧璨。僧璨晚年于安徽司空山传衣钵于四祖道信。道信于唐武德元年(李渊长安称帝那年)在湖北黄梅双峰山(今黄冈市黄梅县)传衣钵于五祖弘忍。可直到弘忍法师,禅一直都是一个小圈子文化,禅的思想没有从寺庙走向民众,禅的文化氛围没有形成。但是,五祖弘忍,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,就是发现了六祖惠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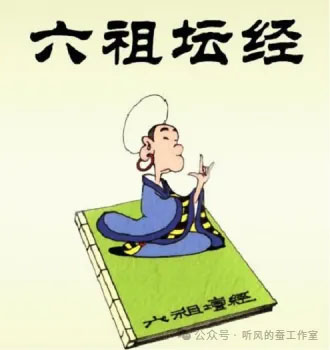
六祖俗姓“卢”,祖籍范阳,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州。其父在涿州当差犯了事,充军到岭南新州,惠能于唐贞观十二年出生在岭南。惠能出生没几年,其父离世,家里也缺衣少吃。迫于生计,他自己打小砍柴卖柴为生,所以他没钱也没空去学私塾,不认字。
惠能打记事儿开始卖柴,这一卖就到了二十多岁,当然了,家庭条件不好,干脆没讨媳妇。这一天扛着柴火,在路过一个大户人家时候,听见一人念叨着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,当时惠能一个愣怔停下脚步,一问那人,说是《金刚经》,湖北黄梅山上有弘忍禅师会讲佛法。
这一问不要紧,好像一颗火星点燃了惠能内心中堆积的木柴,顿时升腾起一种无比强大的内驱力,他留了点盘缠,把这些年攒的家底儿全给了一个同乡好友,以安顿母亲。于是,他独自一人迈步去了湖北黄梅,有句话怎么说得来着?踏上取经路,比抵达灵山更重要!
道场上,惠能见到了弘忍法师,一句“佛性本无南北”,让弘忍法师赞叹“此獦獠根性大利!”为守护禅宗法脉,弘忍点到为止,让惠能到后勤处舂米,一干就是半年多,这期间弘忍法师就没再见他。
再后来,弘忍法师出题,就有了舂米人与首座大弟子神秀写偈子的故事。
只见神秀作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。”
惠能一听,这味儿不对啊!
于是央求了一个会写字儿的,随即在旁边墙上写下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”弘忍法师看到后脱下鞋子,默不作声用鞋底将此偈擦去,说道“亦未得悟!”
说是这么说,擦掉偈子的第二天中午头,趁着众人午休,弘忍自己悄么悄来到了米房,问惠能:“米熟也未?” 惠能答 “米熟久矣,犹欠筛在”。这儿翻译翻译,你准备好了吗?答曰:时刻准备着,就差您点播去芜!
弘忍闻言,没有再说话,只是拿起锡杖敲了三下舂米的石臼,惠能目送师父离开后,夜半三更进了弘忍法师禅房。哎,这个桥段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,对!《西游记》悟空学七十二变那段儿是有历史原型的。
得衣钵后,惠能为避难,按师父嘱托隐姓埋名十五载,这期间,神秀一直围着长安周边开讲座,并通过弟子或信众对外声称,神秀首座早在弘忍法师圆寂前就得了真传,只不过没有公布,而南方那个自称六祖的,只是偷去了衣钵的一个后勤人员,乃至于神秀后来被武则天迎回洛阳成了国师。对此,惠能并不争辩。
由于亲身经历了争夺衣钵的种种苦难,六祖决定不再传衣钵于后人。由于惠能的有教无类、广开法门,让禅宗得以一门五宗、遍布全国。禅,从一种官学神学接了地气,成了普通民众修身养性的思维训练,一时间,岭南周边连卖点心的老妪也会诵经参法了。比如,“下下人有上上智,上上人有没意识。”“离世觅菩提,恰如求兔角。”这是什么意思?劳动人民拥有最高的觉悟和最先进的创造力,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。脱离了生活的觉悟,就是空中楼阁,那才是虚幻。
于是,修禅修心也离不开劳动,这就有了后来的《百丈清规》,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”,农禅合一,不是为了修行而种地,也不是为了种地去修行,种地也罢,打拳也好,甚至抄经诵读,都只是认识外在、反照自己的方便门而已。
毛主席很喜欢读《六祖坛经》,他的秘书林克回忆道:“毛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惠能,《六祖坛经》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。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惠能的身世和学说,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。”1959年10月,毛主席同十世班禅大师谈话中说道,“佛经也是有区别的,有上层人的佛经,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,《六祖坛经》就是劳动人民的。”
六祖惠能将禅的思想融入中国的这片广袤土地,是真正的中国佛学的开创者。他的思想影响深远,中华传统文明精神内核中,儒释道一体的“释”大多源自惠能,以至于后来的阳明心学也是继承了禅宗曹洞宗的理念,日本的稻盛和夫管理学思想、茶道和侘寂文化中都有着中国禅宗深刻的烙印。
五、喫茶去
在六祖的年代,神秀在北方讲禅,他主张渐悟,好像觉悟是一个登山采药的过程,只有一步一步走到山巅才能看到祥云日出。而惠能在曹溪布道,主张顿悟,只要一个人“明心见性”,他就成为觉悟者。抛开对错,哪种主张更接近佛陀的禅心呢?上面不是说过了拈花微笑的事例了么?当你会心一笑,并不需要讲什么,你的心和佛心在刹那间就一体相通,毫无二致。如果觉悟像登山,那就有了程度差异,有人是一里地,有人是五十里,有人在山脚、有人在山腰、有人在山顶。于是在山腰的人,就显得比在山脚的人更高阶,这便有了分别心。分别心和禅宗秉持的“同一真性”南辕北辙,由此看来,神秀一脉没有得到“实相无相”的真传,更没有从“有我”的执念中走出来。
有了分别心,人便会从眼耳鼻舌身意这“六识”中受到污染,远离般若智慧。修行者从生活中找到了一种远离分别心的体验方法,喝茶,于是就有了“茶禅”和“禅茶一味”的说法。

说是晚唐时期,当时在河北赵州(今赵县)的观音院里,禅宗临济宗的赵州禅师时年已经一百多岁了,有两位行脚僧慕名而来,都是远道求法。
赵州问第一个僧人,你来过这儿没有?那人说:第一次来。赵州和尚道:喫茶去。
赵州问第二个僧人,你来过这儿没有?
那人说:我曾经来过。赵州说:喫茶去。
这时候观音院的监寺嘟囔了一句,怎么来过没来过都要去喫茶?
赵州于是唤他的名字,监寺应了之后。赵州对他说:喫茶去。
喫茶和耕地一样,都是世间生活,与修行来说也不过是体验方式而已。如果没有来过觉得自己修行浅,便是分别心,于是喫茶。如果来过,好像喫过禅茶就比没来过的深切,那也有了分别心,可以喫茶。监寺的疑问说明他在喫茶的事儿上执着于外,起了分别念想,好像老学员跟新学员不应该都喫茶,如此,那更要喫茶,反照自己来找回平常心。
摒弃分别心是为了不住相。谁说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,卑鄙是卑鄙者的座右铭?其实,没有什么高尚和卑鄙,高尚和卑鄙是相通并且可以转化的,正如害虫和益虫并非一成不变,附子可以救命、人参可以杀人,都看你什么时候用、怎么用而已,所谓的标准的设定只是一种空相。
对了朋友,到今天,你找到真的自己了么?如果没有善,也没有恶,你心中的自己又是什么样子?
在佛家看来,执着于是非有无的分别心,是烦恼的源泉。好与坏本是一体两面,只看你自己的选择。但请不要误会,佛学这样说,是告诉你一种超脱的看问题视角,不要执着于善恶名相。它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你可以胡作非为,而无所顾忌。相反,即便堕入邪道是一个人的业力使然,那也不是说他不必遭受谴责,善有乐报,恶有苦报,因果不空。佛是让人褪却心魔而实现积极价值的,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“十善业”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”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等等。当一个人不以行善为目的而自发行善的时候,他才是“不著善恶”。对,那是一种叫大德不德的境界。
六、晨钟飞鸟
日出嵩山坳,晨钟惊飞鸟。
中岳嵩山巍峨俊秀,少室山北麓的晨钟暮鼓早已穿越千年,其沉浮起落,让人荡气回肠。
嵩山少林寺自公元495年北魏建寺,经历了六次大浩劫。第一次,公元574年,北周武帝宇文邕认为佛教体系耗散国力,发起灭佛运动,拆了4万余所寺庙,强迫26万余僧尼还俗,少林寺首当其冲,殿宇经像严重损毁。第二次,隋末动乱,少林寺在多方混战中被焚毁劫掠,众僧离散。第三次,公元841年至846年,唐武宗李炎推行“会昌法难”,少林寺殿宇田地全充公,迫使僧众还俗。第四次,满清禁武。清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清朝颁布了禁武令,不让你民间习武,白莲教都快刀枪不入了那能行么?“练习拳棒,易生事端”,汉民会武术、旗人也发怵。至道光年间,少林武学逐渐恢复,但已大不如前。第五次,民国军阀混战。这次最惨烈,因为助力一个俗家弟子樊钟秀争地盘,少林寺卷入纷争。1928年3月,冯玉祥手下石友三攻打少林寺,并下令炮轰寺院,僧众死伤过半。同时,石友三令人浇煤油放火,大火持续40余天,主体建筑如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藏经阁成了焦土;所藏千年经卷、传世拳谱、佛造像几乎尽毁。
第六次,1966年,造反派以“除四旧”名义冲入少林寺,要“砸烂旧世界”。当年戴着袖章的小兵们,一个个怒目圆睁像打了鸡血,于是又出现了火烧少林寺的景象。1966年8月,躁动的人群冲进少林寺,炸毁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等核心建筑,千佛殿、地藏殿、白衣殿的壁画和佛像多被砸毁。千佛殿内明代《五百罗汉朝毗卢》壁画被铁耙刮烂。钟楼、鼓楼、禅堂等建筑被拆,唐代《唐太宗赐少林教碑》、元代《裕公和尚碑》等大量碑刻被推倒砸碎。常住院内陈列的释迦牟尼像等30余尊大型铜像,被熔毁炼钢;数千件青铜法器被砸毁卖了废品。“心意把”“大洪拳” 的全本被烧;“少林活络膏”等古医方配伍失传。
面对暴行,释行正、释素喜等僧众痛心疾首,奋力保护。目前千佛殿大家能看到的几尊铜佛,那是法师拿命换回来的。行正禅师虽目不能视,却以一己残躯横挡在了要捣毁铜佛、炸毁塔林的人群面前。法师知道,他护住的不是浮屠塔的砖瓦,而是少林千年不绝的气运法脉!

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,社会进入思想解放与文化复苏期,长期被压抑的大众文化需求被释放。少林寺真正的转折点也在1982年出现了,李连杰一部《少林寺》在当时一张票一毛钱的条件下,创造了5亿多人观影,1.6亿的票房奇迹。这深深震撼了入寺不久的释永信,也在全球范围内燃起了一场少林文化的热潮!
后续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,如今看来,近日这些纷扰不过是历史的涟漪。行正法师以身护寺不辱使命,他年老之时让永信大和尚光复少林,好比左手指月,不过释永信未能明心见性,反而心随境转。他渐渐发现,自己无法在花花绿绿的俗世和空明静雅的佛门穿梭间给自己安心,也渐渐忘记了那禅心所指不是所谓世间明月,而是人心所向。
但风雨过后必有彩虹,只要心印流长,即便再过千年,少林也还是那个少林。
文/爱写字的钢镚
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赞赏,咱们烈隐新品即将上线,大家可以期待一下~
蚕丝们!蚕哥VIP基地粉丝群已经开放了,现在,长按下方二维码加入粉丝群,就能解锁专属“情报站”!在这里,不仅能和超多蚕粉零距离互动讨论,还有神秘彩蛋不定期掉落,更有独家每日资讯分享!快来,一起加入吧!

作者:听风的蚕朱唯一 2025年08月03日 14:15 河南